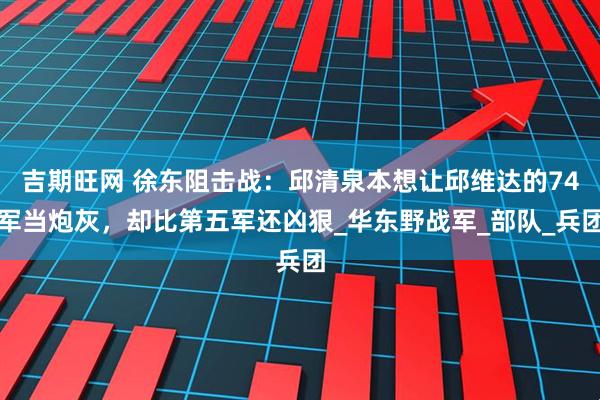
1947年后,邱清泉对邱维达所率领的74军的看法早已发生了变化。在他眼中,这支部队已经不再是抗战结束后的那支精锐部队。特别是在经过1947年那场惨烈的战斗后,74军几乎全军覆没,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兵都在战斗中牺牲,原本装备精良的武器也早已落入华东野战军的手中,成为他们的新型武器。所以,当邱清泉得知74军被编入第二兵团时,他并没有感到任何的喜悦,反而认为这支部队可能成了负担,甚至觉得它无用且拖累他。
当时,邱清泉心中有一支更为依赖的部队——第五军,那是他最初建立威信的部队,他始终认为这才是他真正的“王牌”。而至于74军,他更是把它当作一个充当炮灰的角色,认为它无力改变战局。这样的心态,也反映在了他后来的作战决策上。邱维达对于邱清泉的态度颇为不满,他多次在给老长官王耀武的信中提到自己被冷遇的感受,并认为邱清泉对他的部队心存偏见。为了证明自己,邱维达急于向邱清泉证明,自己所领导的74军依然有着足够的战斗力。
展开剩余72%1948年深秋,徐州“剿总”司令部内,一盏昏黄的灯光下,地图上弯曲的战线指引着一场新的战斗即将打响。邱清泉用冷静的语气指出:“邱维达,74军从双沟绕到敌后,与正面部队合围。”邱维达听后,心中不禁一紧,知道自己将面临一场艰难的任务。这道命令发出时,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,邱清泉似乎已作出决定,完全不考虑部队的实际情况。邱清泉认为,这支才刚重建不久的74军,几乎全由新兵构成,战斗力大打折扣,甚至连团营一级的军官也大部分是1947年那场战役的幸存者。
邱清泉的判断并非没有依据。当黄百韬的第七兵团被围困在碾庄,危在旦夕时,邱清泉坐镇徐州东郊,手中拥有十万兵力,却依旧保持冷静的态度,丝毫不急于支援。他轻描淡写地回应了“剿总”的催促:“黄百韬撑不过五天,冒险不值。”他的言辞中透露出一股精心算计的意味,仿佛在试探着战场上的局势。邱清泉的第二兵团,尽管有着名为第五军的强大核心,实际情况并不如外界所见。他明白,自己的起家部队第五军才是他能依靠的“压舱石”,而其他部队的情况相对薄弱,尤其是74军。
当杜聿明提出抽调一支部队执行关键的迂回任务时,邱清泉毫不犹豫地将74军推了出去。在参谋长李汉萍看来,邱清泉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,他笑着摇头私下感叹:“这差事本该是第五军去,然而邱司令怎会让心腹部队冒险?”于是,邱维达带领的74军便成了这一场艰难任务的主角。
那么,74军真如邱清泉所认为的那样,成了一个脆弱的“杂牌军”吗?实际上,74军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坚韧与历史。1947年孟良崮战役后,74军全军覆没,伤亡惨重,但在重建时,得以幸存的几支新兵团与榴弹炮营成为了其骨干力量,加上伤员归队和新募兵员,兵力迅速恢复至两万余人。虽然装备不如鼎盛时期,但在华东战场上,74军的装备相较于那些频繁遭到重创的部队,仍算得上中等偏上。而更为重要的是,74军在抗战中的顽强生命力并未消失,曾在淞沪、南京、徐州、万家岭等战役中浴血奋战,屡次在重创后迅速重整旗鼓,展现出非凡的战斗韧性。
1948年11月15日深夜,潘塘镇,夜色如墨,远处枪炮声轰鸣。74军与华野苏北兵团在黑暗中碰撞,战争的硝烟弥漫,双方激烈交火,局势一度混乱不堪。74军的51师在华野2纵的猛烈攻击下,伤亡惨重,撤退至刘塘、赵洼防线。此时,华野兵团发起了疯狂的进攻,但74军依然顽强抵抗。华野突袭王塘,尽管干部层接连阵亡,士兵依然义无反顾地冲锋,最终,敌我双方的阵地交错重叠,指挥部前竟有敌军士兵。
邱清泉接到战报时,顿时冷汗直冒。潘塘镇一旦失守,徐州机场的空中命脉将彻底断绝,华野兵团很可能突破后方防线直逼核心区域。为了保住阵地,邱清泉连夜调兵遣将,紧急命令战车营和榴弹炮营增援,仅三小时,龚时英的第32师便顺利增援。尽管华野苏北兵团屡次进攻,但74军在二陈集防线处顽强抵抗,六次进攻皆未成功,74军依旧屹立不倒,成为了邱清泉眼中的“最后屏障”。
潘塘一战,74军的表现超出了邱清泉的预期。这支曾被他视为“弃子”的部队,以惊人的韧性抵挡住了华野的狂风暴雨,最终让邱清泉重新评估了它的价值。事后,邱清泉将74军调往核心防区,而将自己的第五军隐藏在后方,尽量减少风险。尽管最后,邱维达带领的74军在后续的战斗中仍然全军覆没,但与邱清泉兵败身亡不同,邱维达在战后被调入南京的军事学院,成为了我军的一位优待对象。
发布于:天津市领航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